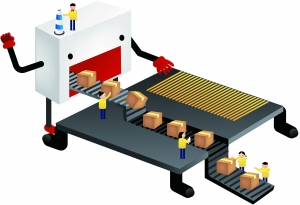作者:錢紅莉
 (資料圖片)
(資料圖片)
一
初來齊魯大地,一趟抵山達海之旅。
小城日照端坐黃昏里,海風拂動,一股股來自大海的咸腥氣息襲來,溫潤清涼。
翌日,拜訪莒州博物館。看館,如翻史書。粗陶、彩陶、漢銅鏡、唐俑,歷代瓷器,無數貨幣,一樣一樣晤面,如切如磋。得見曠世無匹的金縷玉衣一件,靜如處子,遍布幽光。一間間屋子定格著的中國歷史,綿延著時空的廣闊幽深,華夏五千年文明湯湯而過。
在一塊漢磚前佇立,蒼青中沁了一層古直蒼涼的氣質。遠望,猶如一款繡工精湛的涼枕,分布著菱形紋,似乎有著呼吸與體溫;近觀,帶著年深日久的包漿,質感、氣韻好比《漢賦》中的句子,風神俊朗,骨格端正。隔著一層玻璃,縱然無以觸摸,卻也與人秋風頓涼之感。這便是時間留下的痕跡。
古人何以將一塊青磚鍛造得如此精美絕倫,莫非源于心靜?過去的日月沙漏流得慢,時光鐘擺的幅度長而悠,一切都不急,慢慢來……這些年,去過許多古城,訪過許多博物館,每至一處,走著走著,一顆焦躁的心慢慢靜謐、篤定,連呼吸似也變得舒緩溫潤深沉,如若站上時間的荒原,四望無際的綠茵起伏。
二
浮來山,一如我們皖地的敬亭山,海拔不甚高,既不奇崛,亦不秀險。可是,它何以著名?
因為獨一無二的劉勰。
浮來山深藏一座定林寺,為劉勰晚年抄經處。
浮來山之于劉勰,敬亭山之于李白,赤壁之于蘇軾,小石潭之于柳宗元,岳陽樓之于范仲淹……因為劉勰、李白、蘇軾、柳宗元、范仲淹,原本平凡普通的山水亭臺也不朽了起來。
邁過定林寺的第一道門,一株四千歲銀杏蒼翠迎人,神一般緘默。一地綠蔭下,我們這些小小的人抬頭望天,頭頂依然是夏商周時期鈷藍的天,也是先秦兩漢的天、魏晉南北朝的天、隋唐宋元明清的天……山海日月宇宙星辰的恒常中,如蟻的人消逝了一茬又一茬。世事流變里,在一株古老的大樹面前,人類不得不低下頭,謙卑起來。
劉勰當年的抄經小屋,坐落于寺后一個不起眼的角落。抄經人劉勰縱然早已不在,但他卓越的才華使得這間逼仄的小屋熠熠生輝。劉勰是不朽的,一部《文心雕龍》影響深遠,衍生出“龍學”,至今仍有一代代海內外學人,為之皓首窮經。
最為敬服的,是劉勰內心的靜定,偏居一隅,安守清貧孤獨,埋首學問之中。古往今來,集大成者,哪一位不是耐得住寂寞之人?
寫散文長達二十余年,第一次讀《文心雕龍》,仿佛知音之遇。原來,我們自古就是散文的國度。作為一位卓絕的文學批評家,劉勰一直推崇著語言和心性。散文的后面,永遠站著一個人,一個鮮活的人——文為心聲。自一個人的散文中,最能看出其心性。
在《文心雕龍》中,我讀到了“虛靜”這個詞。什么是“虛靜”?想起美國作家喬納森·弗蘭岑說的:“你靜坐時,比追逐時看見更多。”
劉勰歷經數載,潛心完成《文心雕龍》,孑然而終,踐行的一直是“虛靜”。
他的美學思想、史學思想、文學思想、哲學思想,何等超前:“意翻空而易奇,言徵實而難巧也”“情與氣偕,辭共體并。文明以健,珪璋乃聘”“是以怊悵述情,必始乎風;沉吟鋪辭,莫先于骨”“積學以儲寶,酌理以富才,研閱以窮照,馴致以繹辭”……
如何把文章寫好?我想,倘若引用劉勰的話,便是“感物吟志,莫非自然”。再引申一些,即胸中有丘壑,下筆當有神。“丘壑”哪里得來?不過是一日日的積累罷了。
寫散文,最是消耗心神。年深日久,也是一種囚籠,但也無悔。日日與漢字為伍,注定是一種執手偕老的行旅,也是一場萬花怒綻的人生。
浮來山定林寺老了,舊了。古銀杏毗鄰處,豎一石碑,有漢唐氣象,鐫刻的漢字、佛像,被風雨侵蝕,均已模糊。門檻、石欄,正一點點朽壞著。其中一間磚木結構的小屋門楣上,懸一匾額,上書“亙古一人”。
錫箔一樣的烈陽下,駐足這泛著青銅綠的漢字前,拜了一拜……想必是后來的知音寫給劉勰的。一個渺小的人,因為文筆之華彩,足以媲美于星月,也不朽起來。
三
一行人驅車趕往五蓮縣。
路旁無數矢車菊正值盛花期,一朵朵金黃,猶如一雙雙眼,骨碌碌于夏風里顧盼流轉。原野間站著一株株苦楝,紫花累累。五蓮山近在目前——聳立著的頁巖,一瓣一瓣又一瓣。山與山之罅隙處,綠樹蔥蘢,形如荷之蓓蕾,或許故而得名“五蓮山”。
這山與皖地天柱山如出一轍,系千萬億年地殼運動所致,宛如龔賢、黃公望們畫筆下的山勢,運用的是大斧劈皴,大劈大褶,雄渾如一曲曲古典交響樂。近身看,則幽光滿溢,一派舊時代的雍容端肅。這樣的山中,適合壘筑一間容膝齋,接待陶潛、竹林七賢、三曹、李杜……
我最愛的蘇軾,當真來過。
山中罕無人跡,沿途遍布忍冬,黃的花,白的花,如星如螢。野杏樹無數,花落,杏出。鼠曲草起了淺黃薹花,微風中顛顛然,茸茸可愛。野艾的藥香氣,一路追隨著我們。
終于抵達白鶴樓遺址。歷經康熙年間一場地震的摧殘,白鶴樓已潰成廢墟。一塊三四米見方的巨石,平滑如硯臺,留有大小不一的圓形空洞。巨石上唯余“白鶴樓”三個字,據傳為蘇軾手跡。密州時期的蘇軾,正值壯年,尚未遭遇黃州時期那樣的滅頂之災,寫起字來有躍躍欲試的揚眉之氣。
跨度兩年余,于密州主政一方的他,公務之余,創作詞作二百余首,最不朽的三首,分別是悼念亡妻的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》、思念弟弟子由的《水調歌頭·明月幾時有》和《江城子·密州出獵》。這首《密州出獵》,有“千騎卷平岡”的飛揚開闊,以及“酒酣胸膽”的癲狂恣意,也是蘇軾沉郁顛沛的一生中,少有的流露出豪氣干云的詩作。有人說,《密州出獵》正是蘇軾短居白鶴樓時所作——五蓮山下平原風貌,像極詞中的“千騎卷平岡”。而在唐宋時期,五蓮山系涵容于密州域內。
斜陽余暉中,眺望山下,平原緬邈。廢墟上,盤桓久之,不舍離去。有一分惆悵,似林中冷泉一線,淡淡淺淺地來。
四
莽莽蒼蒼的原野中,新麥初黃。當日正值小滿。
山下一座小小的村落,如若獨立世外,家家門前植有玫瑰,紅的花,黃的花,白的花,簇新而妍麗。老婦人三兩,坐在門前矮凳上,閑閑地望著匆匆疾步的我們——在她們滄桑的臉上,有一種祖母的從容古雅,淡淡流瀉。
一生與山在一起的人,為“仙”,靈魂上守住了一分靜定自閑——是依山望月的閑,也是忙碌奔波的城里人一生求而不得的閑。
村口歇有一位年輕女子,她面前一只竹籃,盛滿桲欏葉,還有一扎藺草,說是用來裹粽子的。是的,端午迫在目前了。只要在中國的土地上,無論走到哪里,風俗人情都能讓來自不同地方的人,彼此的心相連。
五蓮山下的原上,遍布櫻桃樹。有些婦女挎只竹籃,一身簡樸衣裳,悠閑地站在樹下采摘鮮鮮妍妍的櫻桃。有些婦女坐在路旁,面前擱一籃紅櫻桃、一籃黃櫻桃,靜等顧客。這款艷麗浪漫的時令水果,輝映著那一張張淳樸自然的臉龐,分明是一幅幅塞尚的靜物畫。
斜陽欲墜間,車穿過麥田,拐至一條小河邊。石橋畔,一年輕女子臨水浣洗。雙肩一下一下富于韻律地聳動著,腳上沒入淺水的一雙潔白無瑕的靴子宛如兩只白鴿。一人,一橋,一河漣漪,令我一再回望。
五蓮山腳下,存有石屋一座,名曰“丁家祠”。這座屋子奇特的地方,在于屋基、屋墻、屋壁、屋瓦,均為條石所構,共計一百零八塊。一腳踏入,頓感沁涼通泰,如浸清泉,耳畔似流水渙渙。石壁間嵌有黑碑若干,字跡均模糊不辨。據考證,此屋曾為蘭陵笑笑生所有,他本姓丁。
驚喜不絕,這也是旅行的魅力所在。
五
一整日,經兩座縣境,自莒州,上浮來山,訪劉勰抄經處,再往五蓮縣,過五蓮山,尋蘇軾遺蹤。黃昏,歇日照近郊白鷺灣。一路水綠山青,鷺鳥蹁躚,如在江南。
中午在高興鎮鎮政府用餐。由于暈車,胃內翻騰,只得掰一小瓣煎餅囫圇吞咽。末了,問廚房要一只食品袋,想將剩下的煎餅帶上車吃。一小會兒工夫,好客的他們竟為我拎來一捆煎餅,足足十余張。
憶起五六年前,一位山東讀者給我留言:“因為讀過你的書,知道你的胃不好,想給你寄些煎餅養胃。”面對她殷切的美意,我婉拒了,又深覺無以回報。
這世間,人與人之間的情誼,因為珍稀,所以倍感珍惜。
回廬后,家務間隙,忽感饑餓時,便拿出這一沓蒼灰如古宣的煎餅,掰一小牙,靜靜咀嚼,齒間有小米、玉米、高粱混合的香氣流瀉。每次吃這來自齊魯之地的平凡食物,總叫人想起“童年”“故鄉”“遠方”這些令人終生溫暖的詞。
《光明日報》( 2023年06月09日?15版)